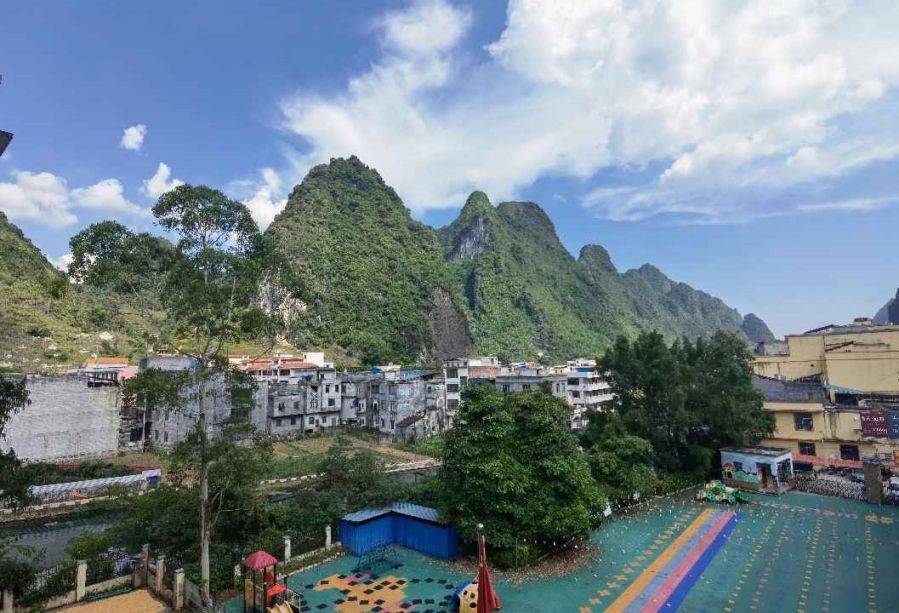支教也要講清楚書法的皮肉與筋骨
有個在某興趣班學過書法的小朋友在書法課開始之前很興奮,要展示給我們看他的水平:寫橫的時候毛筆應當怎樣轉,哪一處需頓一下,哪一處需提起來,寫豎的時候又應當怎樣,等等。我說:“你學的是顏真卿吧,我看這些筆畫的樣子就知道了。”
 他很開心,認為我是表揚他。我當然不是在表揚他。顏真卿的楷書被很多書法大家認為寫出了盛唐氣象,極其完美,讓無數初學者苦臨數年仍不得精髓卻也樂在其中。好的楷書即使放大至臉盆大小依舊端莊,絲毫不散亂,但是看他的字:無需放大,站都站不穩,只是某些筆畫有一點顏體的皮肉相。
他很開心,認為我是表揚他。我當然不是在表揚他。顏真卿的楷書被很多書法大家認為寫出了盛唐氣象,極其完美,讓無數初學者苦臨數年仍不得精髓卻也樂在其中。好的楷書即使放大至臉盆大小依舊端莊,絲毫不散亂,但是看他的字:無需放大,站都站不穩,只是某些筆畫有一點顏體的皮肉相。
這并不是個別現象。很多人學書法是奔著筆畫去的,很多老師重點教怎樣寫好筆畫的形狀,很多人欣賞書法關注的不過是“這一捺很有氣勢”之類的東西。至少在我觀察到的范圍里面,少有人評價:“這個字的結構真好”,字的間架結構乃是書法藝術的筋骨,筋骨不存,皮肉焉附?
支教這幾天,除了科學課,我還講篆刻,詩書畫印為文人四藝,要懂印先要懂詩書畫。
我認為,書法入門不應該局限在唐楷,更不應該只盯著顏體。書法入門應當有兩大任務:一是培養正確的審美觀,知其所以然;二是訓練學員對毛筆的掌控能力,知其然。如果只盯著少數幾種字體看,沒有對比,怎么培養審美能力,怎么透過皮肉相看到筋骨相呢?
筋骨相的形成以書者的思想為依托。比如漢代的隸書《禮器碑》,沖天的尖銳“燕尾”用略向下的圓潤“蠶頭”來平衡,體現出當時書者強烈的書法表現欲,而整體端莊扁平的結構,則體現出時人對毛筆用法的稚嫩探索、對文字的敬畏。比如懷素和尚的狂草《自敘帖》,如大江大河波濤滾滾,這是扎實的歐楷基本功給他的底氣,浩瀚的精神世界給他的意氣。比如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厚重處渾樸蒼穆,細勁處筋骨凝練,轉折處有化繁為簡,也有殺筆狠重,連綿處又痛快淋漓,江河直下,筆法之豐富令后人望塵莫及,但每個字蘊含的思想都一樣:悲憤。
筋骨相形成以后,才可以形成皮肉相。歐楷險絕,褚楷空靈,顏楷厚重,柳楷遒勁,同為唐楷,但是這四種字體的間架結構有明顯的區別,單說走之在某一個字里和其他筆畫的空間關系,不同字體就有不同的答案。書法家寫出來的筆畫必須服務于他心里的間架結構,如果把褚楷的筆畫放到歐楷的結構身上,那會形成一種看著就別扭的字體。筋骨是根本,皮肉是從筋骨上長出來的。
我一直盯著楷書講,因為我認為,要體悟書法的筋骨相,要想透過皮肉相看到筋骨相,應當從正書入門。正書是指篆書、隸書、楷書,是書法的“站”。行書為“走”,草書為“跑”,在我看來都不適合給初學者書法審美打基礎。曾有老先生攜草書作品請當代草書大家林散之指教,散翁一張一張認真翻看,只點頭不說話。老先生走后,林老說:“這個人還在門外轉。”他說如果來訪者是小青年,他一定毫不猶豫讓他剎車,趕快寫楷書。但老先生走了一輩子彎路,叫他從頭練楷書,一則使其難堪,二則為時已晚,故只能緘口不言。入門是剛開始,不是已經走了很久彎路,當然應該從正書入門,而以我國書法教育的現狀,能接觸到楷書教育已經算造化,就不要奢求篆書和隸書了。
現在很多人只看皮肉相不看筋骨相,這不是好事。曾有同學給我看他設計的印章稿,是一幅細朱文的“禪定”,為了體現他的美術功底,“禪”字的右邊一半被抽象成燈籠,那一豎正是燈籠的穗子,彎斜作風吹狀,且下面半截留白,表示懸于半空,我說你這叫什么禪定呢?風吹就動,懸空不寧,只管好看,不顧內涵。

這并不是個別現象。很多人學書法是奔著筆畫去的,很多老師重點教怎樣寫好筆畫的形狀,很多人欣賞書法關注的不過是“這一捺很有氣勢”之類的東西。至少在我觀察到的范圍里面,少有人評價:“這個字的結構真好”,字的間架結構乃是書法藝術的筋骨,筋骨不存,皮肉焉附?
支教這幾天,除了科學課,我還講篆刻,詩書畫印為文人四藝,要懂印先要懂詩書畫。
我認為,書法入門不應該局限在唐楷,更不應該只盯著顏體。書法入門應當有兩大任務:一是培養正確的審美觀,知其所以然;二是訓練學員對毛筆的掌控能力,知其然。如果只盯著少數幾種字體看,沒有對比,怎么培養審美能力,怎么透過皮肉相看到筋骨相呢?
筋骨相的形成以書者的思想為依托。比如漢代的隸書《禮器碑》,沖天的尖銳“燕尾”用略向下的圓潤“蠶頭”來平衡,體現出當時書者強烈的書法表現欲,而整體端莊扁平的結構,則體現出時人對毛筆用法的稚嫩探索、對文字的敬畏。比如懷素和尚的狂草《自敘帖》,如大江大河波濤滾滾,這是扎實的歐楷基本功給他的底氣,浩瀚的精神世界給他的意氣。比如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厚重處渾樸蒼穆,細勁處筋骨凝練,轉折處有化繁為簡,也有殺筆狠重,連綿處又痛快淋漓,江河直下,筆法之豐富令后人望塵莫及,但每個字蘊含的思想都一樣:悲憤。
筋骨相形成以后,才可以形成皮肉相。歐楷險絕,褚楷空靈,顏楷厚重,柳楷遒勁,同為唐楷,但是這四種字體的間架結構有明顯的區別,單說走之在某一個字里和其他筆畫的空間關系,不同字體就有不同的答案。書法家寫出來的筆畫必須服務于他心里的間架結構,如果把褚楷的筆畫放到歐楷的結構身上,那會形成一種看著就別扭的字體。筋骨是根本,皮肉是從筋骨上長出來的。
我一直盯著楷書講,因為我認為,要體悟書法的筋骨相,要想透過皮肉相看到筋骨相,應當從正書入門。正書是指篆書、隸書、楷書,是書法的“站”。行書為“走”,草書為“跑”,在我看來都不適合給初學者書法審美打基礎。曾有老先生攜草書作品請當代草書大家林散之指教,散翁一張一張認真翻看,只點頭不說話。老先生走后,林老說:“這個人還在門外轉。”他說如果來訪者是小青年,他一定毫不猶豫讓他剎車,趕快寫楷書。但老先生走了一輩子彎路,叫他從頭練楷書,一則使其難堪,二則為時已晚,故只能緘口不言。入門是剛開始,不是已經走了很久彎路,當然應該從正書入門,而以我國書法教育的現狀,能接觸到楷書教育已經算造化,就不要奢求篆書和隸書了。
現在很多人只看皮肉相不看筋骨相,這不是好事。曾有同學給我看他設計的印章稿,是一幅細朱文的“禪定”,為了體現他的美術功底,“禪”字的右邊一半被抽象成燈籠,那一豎正是燈籠的穗子,彎斜作風吹狀,且下面半截留白,表示懸于半空,我說你這叫什么禪定呢?風吹就動,懸空不寧,只管好看,不顧內涵。
時間:2022-06-22 作者:多彩大學生網 來源:多彩大學生網 關注:
- 廣西計劃補錄200名大學生西部計劃志愿者
- 8月19日,記者從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廣西項目管理辦公室獲悉,即日起至8月29日24時,我區將面向全國普通高等學校2022年應屆本科畢業
- 08-20
- 江蘇2839名大學生志愿者奔赴支援西部和鄉村振興一線
- 8月10日,2022年江蘇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鄉村振興計劃”出征儀式在南京農業大學體育館舉行
- 08-13
- 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累計選派46.5萬余人
- 近日,各地陸續組織開展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簡稱西部計劃)志愿者出征儀式,3.67萬名新招募志愿者赴中西部地區基層開展志愿服務。
- 08-13
- 鄉村振興,我們在路上
- 本人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第24屆研究生支教團的團長宋佳銘,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都安縣的地蘇鎮進行支教。根據廣西項目辦的要求,本人
- 08-04
- 青春不敗 映山紅遍
- 7月11日,結束了最后一門考試后,安徽師范大學“映山紅”暑期社會實踐團隊正式踏上了赴往安慶市楊橋鎮的旅程,開始了為期十五天的暑期
- 07-05
- 支教不分遠近,真心難能可貴
- 我記得曾經看白巖松先生寫的書,書中論述了“身邊的志愿行動”的重要性。如今我們社會中,太多的志愿者爭先恐后地趕往祖國邊遠地區甚至
- 07-05
- 無遠弗屆,熱愛可抵歲月漫長
- 只有實際生活中可以學習,只有實際生活能教訓人,只有實際生活能產生社會思想。
- 07-05
- 關愛留守兒童,展現π遞數學情
- 拜倫曾說過:“百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人生最美好的時光莫過于擁有青春的時刻,每個青年人都有屬于自己的青春主張。
- 07-05
- 多彩大學生網©版權所有 客服QQ:471708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