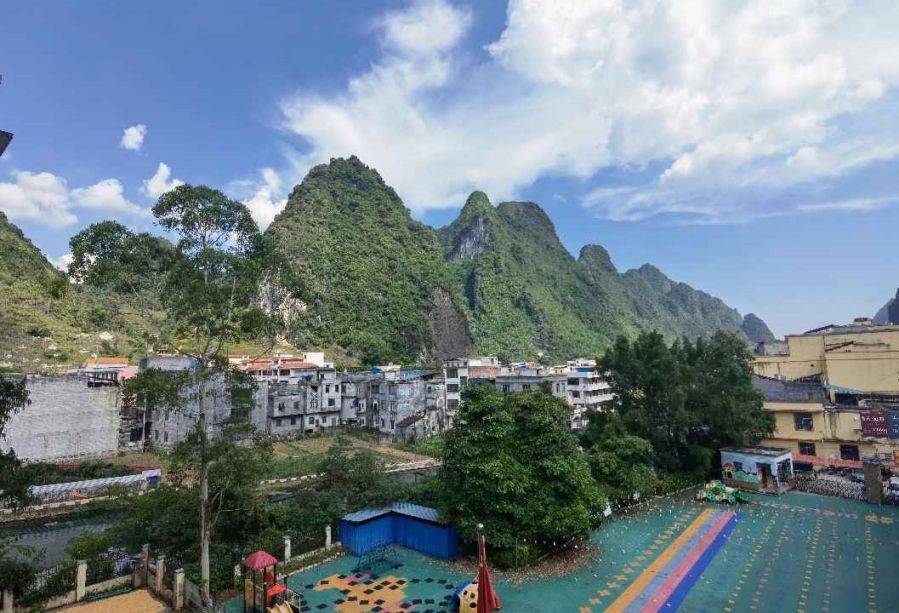光影之中猶見兒時,直面鏡頭更期未來
2021年7月19日至28日,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和光支教隊的14名同學從五湖四海匯聚到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雙浮鎮開展支教活動,并于期間前往當地前進村展開留守兒童主題調研活動。在當地團縣委、村委會及群眾的全力支持下,活動反響熱烈,效果顯著。

“你真的是一個合格的攝影師。”
“不,我只是一個記錄者罷了。”
貫穿整個支教,這樣的對話幾乎每天都會出現。說實話,我也有些無奈。作為支教隊宣傳組的成員,或許大家經常看到我扛著笨重的機器,在支教現場的各處角落里手忙腳亂,身怕錯過每一個精彩瞬間,才會這么說的吧。所以,我把這種評價更看作是大家對我敬業精神的肯定與贊許。但我必須承認,我并沒有刻意追求“合格的攝影師”的稱號,只是充當一個記錄者的角色,用鏡頭去捕捉光影流動的美感,從取景器中窺見無與倫比的瞬間,不矯揉造作,不有意粉飾,“一看平平無奇,再看意蘊無窮”,如此足矣。
時間回溯到我報名支教的前夕,記得我當時正重讀柴靜的《看見》,在《雙城的創傷》一章駐足良久。那一章講述的是若干名鄉村兒童由于愚昧與麻木選擇集體服毒,最終給社會留下了一個難以愈合的傷疤——兒童,尤其是鄉村兒童,心理問題亟需引起足夠重視。柴靜寫過這么一句話:“最后,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
回想我的童年,我似乎永遠活在溫室里,家人的關懷,老師的呵護,同學的幫助,陽光、笑臉、棒棒糖構成了我生活的全部詞匯。但這并不妨礙我的奇思妙想,可能也經常冒出一些奇怪的甚至是極端的想法出來,但我會悄悄告訴身邊的人,他們也總會聆聽我的秘密,并給我心靈上的指導,告訴我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萬萬不可取的。我們常常把“竭盡全力呵護孩子們的幼小心靈”掛在嘴邊,可是真的讓我們自己去呵護、去關懷時,往往又顯得局促不安、無從下手。
但是,機會來臨時,又何嘗不試試呢?于是,當我看到群里轉發的支教活動時,毫不猶豫地報了名,并一路過關斬將,順利成為和光支教隊的一員。不過,這一次,我并不是以老師的身份,而是以一個局外人——記錄者的身份走進安徽阜陽市太和縣雙浮鎮的一所鄉村留守兒童中心。之所以說是局外人,是因為我不想因為情緒或感情問題影響孩子們在鏡頭下的自然表現和真實流露,該什么樣就什么樣,“只記錄不說話”,用鏡頭訴說我所想表達的東西。
其實,我也有過暗暗擔心。記得支教面試時,面試官問我一個問題:“如果孩子們害怕鏡頭,你會怎么辦?”我沉默片刻,“孩子們不會害怕鏡頭的,鏡頭只會讓孩子們變得更加自信、更加真實。”一無所知的我卻語出驚人,當時甚至把自己給逗笑了。但事實證明,我說的并沒有錯。
我有發現,同一節課上,前二十分鐘孩子們可能對我的相機投以好奇、熱烈的目光,當鏡頭懟臉時卻又顯得很羞澀與安分。然而,后二十分鐘往往又與前半段課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場景,有好一部分的孩子面對鏡頭都變得甚是自然,甚至有些大膽的孩子會活躍地爭搶著朝鏡頭打招呼,讓我有種說不出來的驚喜與感動。
但說起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說是我來到雙浮鎮遇見的第一個孩子。當時,我和幾個隊友是第一批來到小鎮上的。剛收拾好行李安頓下來,我便碰巧在食堂附近遇到了一個小男孩在和另一個弟弟捉青蛙,這不禁讓我想到少年閏土捕猹時的場景。我細細打量著他,那男孩瘦瘦的,黑黑的,身手卻矯健著哩。他對著鏡頭給我一個毫無違和感的甜甜的微笑,是我在支教期間見過的最美的微笑。
敢于面對鏡頭,正視鏡頭,甚至朝鏡頭比個心、招招手,亦或是露一個微笑,無疑見證著孩子們的成長,也讓他們在未來面對鏡頭面對觀眾時找尋回昔日的自信與獨立,不裝不演,真實自然,這也是我作為支教記錄者所希望看到的。

“你真的是一個合格的攝影師。”
“不,我只是一個記錄者罷了。”
貫穿整個支教,這樣的對話幾乎每天都會出現。說實話,我也有些無奈。作為支教隊宣傳組的成員,或許大家經常看到我扛著笨重的機器,在支教現場的各處角落里手忙腳亂,身怕錯過每一個精彩瞬間,才會這么說的吧。所以,我把這種評價更看作是大家對我敬業精神的肯定與贊許。但我必須承認,我并沒有刻意追求“合格的攝影師”的稱號,只是充當一個記錄者的角色,用鏡頭去捕捉光影流動的美感,從取景器中窺見無與倫比的瞬間,不矯揉造作,不有意粉飾,“一看平平無奇,再看意蘊無窮”,如此足矣。
時間回溯到我報名支教的前夕,記得我當時正重讀柴靜的《看見》,在《雙城的創傷》一章駐足良久。那一章講述的是若干名鄉村兒童由于愚昧與麻木選擇集體服毒,最終給社會留下了一個難以愈合的傷疤——兒童,尤其是鄉村兒童,心理問題亟需引起足夠重視。柴靜寫過這么一句話:“最后,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
回想我的童年,我似乎永遠活在溫室里,家人的關懷,老師的呵護,同學的幫助,陽光、笑臉、棒棒糖構成了我生活的全部詞匯。但這并不妨礙我的奇思妙想,可能也經常冒出一些奇怪的甚至是極端的想法出來,但我會悄悄告訴身邊的人,他們也總會聆聽我的秘密,并給我心靈上的指導,告訴我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萬萬不可取的。我們常常把“竭盡全力呵護孩子們的幼小心靈”掛在嘴邊,可是真的讓我們自己去呵護、去關懷時,往往又顯得局促不安、無從下手。
但是,機會來臨時,又何嘗不試試呢?于是,當我看到群里轉發的支教活動時,毫不猶豫地報了名,并一路過關斬將,順利成為和光支教隊的一員。不過,這一次,我并不是以老師的身份,而是以一個局外人——記錄者的身份走進安徽阜陽市太和縣雙浮鎮的一所鄉村留守兒童中心。之所以說是局外人,是因為我不想因為情緒或感情問題影響孩子們在鏡頭下的自然表現和真實流露,該什么樣就什么樣,“只記錄不說話”,用鏡頭訴說我所想表達的東西。
其實,我也有過暗暗擔心。記得支教面試時,面試官問我一個問題:“如果孩子們害怕鏡頭,你會怎么辦?”我沉默片刻,“孩子們不會害怕鏡頭的,鏡頭只會讓孩子們變得更加自信、更加真實。”一無所知的我卻語出驚人,當時甚至把自己給逗笑了。但事實證明,我說的并沒有錯。
我有發現,同一節課上,前二十分鐘孩子們可能對我的相機投以好奇、熱烈的目光,當鏡頭懟臉時卻又顯得很羞澀與安分。然而,后二十分鐘往往又與前半段課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場景,有好一部分的孩子面對鏡頭都變得甚是自然,甚至有些大膽的孩子會活躍地爭搶著朝鏡頭打招呼,讓我有種說不出來的驚喜與感動。
但說起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說是我來到雙浮鎮遇見的第一個孩子。當時,我和幾個隊友是第一批來到小鎮上的。剛收拾好行李安頓下來,我便碰巧在食堂附近遇到了一個小男孩在和另一個弟弟捉青蛙,這不禁讓我想到少年閏土捕猹時的場景。我細細打量著他,那男孩瘦瘦的,黑黑的,身手卻矯健著哩。他對著鏡頭給我一個毫無違和感的甜甜的微笑,是我在支教期間見過的最美的微笑。
敢于面對鏡頭,正視鏡頭,甚至朝鏡頭比個心、招招手,亦或是露一個微笑,無疑見證著孩子們的成長,也讓他們在未來面對鏡頭面對觀眾時找尋回昔日的自信與獨立,不裝不演,真實自然,這也是我作為支教記錄者所希望看到的。
時間:2022-06-16 作者:多彩大學生網 來源:多彩大學生網 關注:
- 廣西計劃補錄200名大學生西部計劃志愿者
- 8月19日,記者從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廣西項目管理辦公室獲悉,即日起至8月29日24時,我區將面向全國普通高等學校2022年應屆本科畢業
- 08-20
- 江蘇2839名大學生志愿者奔赴支援西部和鄉村振興一線
- 8月10日,2022年江蘇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鄉村振興計劃”出征儀式在南京農業大學體育館舉行
- 08-13
- 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累計選派46.5萬余人
- 近日,各地陸續組織開展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簡稱西部計劃)志愿者出征儀式,3.67萬名新招募志愿者赴中西部地區基層開展志愿服務。
- 08-13
- 鄉村振興,我們在路上
- 本人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第24屆研究生支教團的團長宋佳銘,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都安縣的地蘇鎮進行支教。根據廣西項目辦的要求,本人
- 08-04
- 青春不敗 映山紅遍
- 7月11日,結束了最后一門考試后,安徽師范大學“映山紅”暑期社會實踐團隊正式踏上了赴往安慶市楊橋鎮的旅程,開始了為期十五天的暑期
- 07-05
- 支教不分遠近,真心難能可貴
- 我記得曾經看白巖松先生寫的書,書中論述了“身邊的志愿行動”的重要性。如今我們社會中,太多的志愿者爭先恐后地趕往祖國邊遠地區甚至
- 07-05
- 無遠弗屆,熱愛可抵歲月漫長
- 只有實際生活中可以學習,只有實際生活能教訓人,只有實際生活能產生社會思想。
- 07-05
- 關愛留守兒童,展現π遞數學情
- 拜倫曾說過:“百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人生最美好的時光莫過于擁有青春的時刻,每個青年人都有屬于自己的青春主張。
- 07-05
- 多彩大學生網©版權所有 客服QQ:471708534